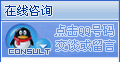“直译”这名词,在“五四”以后方成为权威。这是反抗林琴南氏的“歪译”而起的。我们说林译是“歪译”,可丝毫没有糟蹋他的意思;我们是觉得“意译”名词用在林译身上并不妥当,所以称它为“歪译”。
林氏是不懂“蟹行文字”的,所有他的译本都是别人口译而林氏笔述。我们不很明白当时他们合作的情形是别人口译了一句,林氏随即也笔述了一句呢,还是别人先口译了一段或一节,然后林氏笔述下来?但无论如何,这种译法是免不了两重的歪曲的:口译者把原文译为口语,光景不免有多少歪曲,再由林氏将口语译为文言,那就是第二次歪曲了。
这种歪曲,可以说是从“翻译的方法”上来的。
何况林氏“卫道”之心甚热,“孔孟心传”烂熟,他往往要“用夏变夷”,称司各特的笔法有类于太史公,……于是不免又多了一层歪曲。这一层歪曲,当然口译者不能负责,直接是从林氏的思想上来的。
所以我们觉得称林译为“歪译”,比较切贴。自然也不是说林译部部皆歪,林译也有不但不很歪,而且很有风趣——甚至与原文的风趣有几分近似的,例如《附掌录》中间几篇。这一点,我们既佩服而又惊奇。
现在话再回到“直译”。
照上文说来,“五四”以后的“直译”主张就是反对歪曲了原文。原文是一个什么面目,就要还它一个什么面目。连面目都要依它本来,那么,“看得懂”,当然是个不言而喻的必要条件了。译得“看不懂”,不用说,一定失却了原文的面目,那就不是“直译”。这种“看不懂”的责任应该完全由译者负担,我们不能因此怪到 “直译”这个原则。
这原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,然而不久以前还有人因为“看不懂”而非难到“直译”这个原则,而主张“顺译”,这也就怪了。
主张“顺译”者意若曰:直译往往使人难懂,甚至看不懂,为了要对原文忠实而至使人看不懂,岂不是虽译等于不译;故此主张“与其忠实而使人看不懂,毋宁不很忠实而看得懂”。于是乃作为“顺译”之说。“顺”者,务求其看得懂也。
在这里,我们觉得不必噜噜苏苏来驳斥“顺译”说之理论上的矛盾(因为它的矛盾是显然的),我们只想为“直译”说再进一解:
我们以为所谓“直译”也者,倒并非一定是“字对字”,一个不多,一个也不少。因为中西文字组织的不同,这种样“字对字”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的翻译,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从前张崧年先生译过一篇罗素的论文。张先生的译法真是“道地到廿四分”的直译,每个前置词,他都译了过来,然而他这篇译文是没人看得懂的。当时张先生很坚持他的译法。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译文别人看不懂,可是他对《新青年》的编者说:“这是一种试验。大家看惯了后,也就懂得了!”当时《新青年》的编者陈促甫先生也不赞成张先生此种“试验”,老实不客气给他改,改了,张先生还是非常不高兴。现在张先生大概已经抛弃了他的试验了罢,我可不十分明白,但是从这个故事就证明了“直译”的原则并不在“字对字”一个也不多,一个也不少。“直译”的意义就是“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”。倘使能够办到“字对字”,不多也不少,自然是理想的直译,否则,直译的要点不在此而在彼。
环球